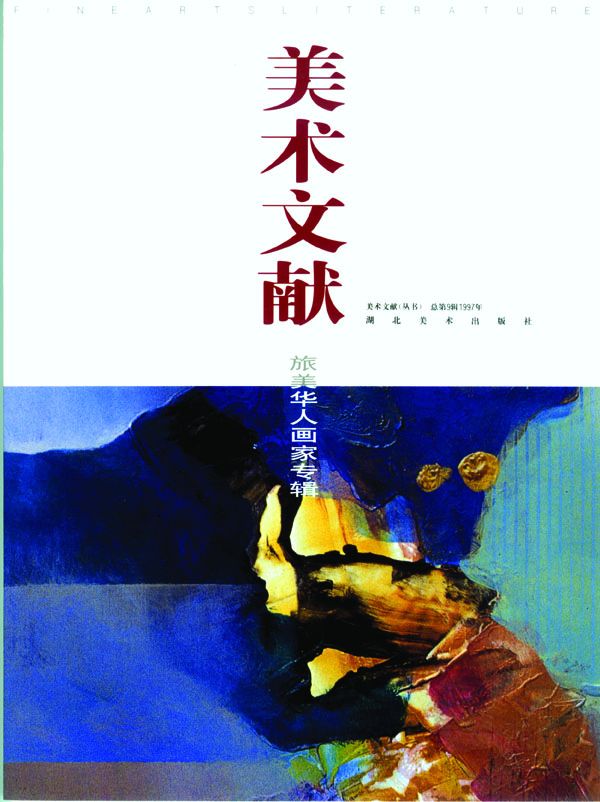第9辑 旅美华人画家专辑(1997年)
学术主持:王受之
主题:蒋铁锋 秦元阅 肖惠祥 潘企群
Issue No. 9 (1997)
Theme: Overseas Chinese Artists
Academic Host: Wang Shouzhi
A.T: Jiang Tiefeng, Qin Yuanyue, Xiao Hui Xiang, Pan Qiqun
海外华人艺术家的历程
王受之
1996年11月美国洛杉矶
1995年底,湖北美术出版社的副社长贺飞白先生来美国访问,我们曾经在洛杉矶一起吃饭,席间他谈他们出版的一套叫作<美术文献》的丛书,目的是探索一些涉及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的专门议题。他带了几本已出版的《美术文献》给我看,当时的确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年来,国内的美术刊物越出越多,然而有份量的理论刊物却仍感缺乏。虽然也有比如《江苏画刊》等一批刊物,不时有些较具挑战性的理论文章出现,但是从总体来看,理论研究的发展有点滞后。而《美术文献》则具有少见的理论深度,在题材的挑选、文章的组织、甚至丛书本身的体例等方面都很有水平,实在是令人高兴。
贺先生在交谈中提出,希望我能够为《美术文献》组织编写有关目前旅居海外的,特别是北美的艺术家专集。不仅仅是因为我长期在美国的高等美术院校担任理论教学和研究,对当代美术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亦因为我与部分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艺术家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和比较和谐的关系。其实,我知道这个工作不但难度很大,而且还会吃力不讨好。首先,因为不可能把所有旅居海外的艺术家全部包括进来,这就有个选择取舍的问题。而中国人的面子总是最重要的,万一取舍不当,便会伤了朋友感情,是很为难的事。而且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美国式的艺术批评,如果仅是写些吹捧文章,就完全违背了艺术评论的基本立场,因此,这个工作对我个人来讲是难得两全的。但是,由于贺先生极力鼓励,而一些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也希望我能够出力介绍,讨论和分析他们的艺术发展历程,盛情难却,因此答应了。虽然事后依然感到困惑,但是原来说好的约稿日期越来越近,而我约好的大部分艺术家也非常积极地在准备作品,只有勉为其难了。其实,无论从自己的能力或者中国式的人际关系的“平衡技术”来讲,我都是难以担当这个重任的。
中国艺术家大批地旅居海外,最早始于本世纪20年代,当时大约有人数过百人的一批艺术家去西方和日本学习美术,比如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勤、常书鸿、倪贻德、司徒乔、吴作人、吕斯白、余本、卫天霖、冯法驷、周碧初、陈报一、孙福熙、潘玉良、汪亚尘、方君璧、孙多慈等等。他们基本是在学业结束之后回国,成为把西方绘画技法引人中国的重要人物,开创了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技巧结合的新阶段。回国之后,不少人从事了西式绘画教学,比如徐悲鸿担任南京的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林风眠担任浙江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颜文樑担任苏州的江苏艺专校长,等等;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而且通过这样的努力,奠定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学和创作的基础,这对于促进西式的写实主义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第二次比较大批的艺术家留学海外是在50年代。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迅速发展自己的写实主义美术,选择了一批中、青年艺术家到当时的苏联留学,基本上是去列宁格勒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其中包括画家、雕塑家和理论家,比如罗工柳、全山石、林岗、郭绍纲、李天祥、肖峰、徐明华、邵大箴等等。他们在苏联通过严格的训练,掌握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绘画技巧,也掌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对于苏联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也理解深刻。这批人大部分在60年代回国,迅速成为全国各个主要美术学院的教学主要骨干。他们与在北京由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主持的油画训练班中的学员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内艺术创作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风格的美术的中坚人物。留苏这一批人和被称为“马训班”的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的成员是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力量,他们当中一些人目前依然在创作,或者担任国内美术教育的领导工作。以上两批外出的艺术家,其实数量都很小,但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艺术发展比较受局限,特别是在强调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留苏的这批艺术家对于奠定整个中国艺术的写实主义模式和艺术院校的教学模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迄今依然存在。
如果从人数来讲,应该说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总数远远不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出国的第三批人多。自从“文化大革命”于1977年结束以来,国内开始有相当多的艺术家移居海外。开始只是为数不多的赴西方留学人员,后来则多出一些其它的渠道,包括以举办自己的展览出国的、以交换学者身份出国的、参加国外的某些展览出国的等等,人数越来越多。虽然目前对于这个时期到底有多少艺术家出国没有确切的数目,但是,根据粗略的估计,人数大约在数百人以上;如果把所有的来自国内的旅居西方的艺术家和曾经从事过与美术有关工作的人(比如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等等)都计算在内,大约人数会到千人左右。其中,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法国的巴黎是人数比较多的集中地区,德国、日本等等国家中的中国艺术家人数也相当多。记得1993年原来中央美术学院为副院长侯一民先生和教授周令钊先生来洛杉矶时,到我家作客,提到在纽约街头画肖像的画家中,中央美术学院和上海油画雕塑工作室的人占大多数,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中央美术学院的总部在纽约,分部在北京,虽然言过其实,但是也不无几分真实。中国艺术家来西方,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东西方的航线上,芝术家总是络绎不绝。
这个第三次中国艺术家旅居海外的高潮,情况与前面两次很不一样:首先,它缺乏组织性。大部分出国的艺术家是通过私人渠道,很少是由国家派出的,因此,这些艺术家所去的西方国家也比以前两次范围广阔得多,他们个人的经历也复杂得多;其二,它缺乏以前两次的大规模回国的影响。大部分这个时期出国的艺术家留在外国,即便回国,也很少有留下工作的;因此,产生了第三个不同方面:他们对于国内艺术界的影响相对来说非常微弱。
第三次中国艺术家去西方的浪潮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只是去看看西方艺术,了解当地西方艺术的情况,或者到收藏丰富的西方主要艺术博物馆中饱饱眼福,之后就回去了。我在美国接待过不少这类艺术家,几乎国内主要美术学院的领导或者教学骨干我都见过;他们大多数都是匆匆而过,其中有正式官方访问性质的,也有纯粹私人访问的。这种访问的结果是非常积极的。通过访问,他们都了解了西方艺术的情况,对于以前只能通过印刷品见到的西方艺术能够仔细地观看和思考,有了感性认识;这种接触,对于破除西方艺术的神秘感、掌握和了解西方艺术的实质内容非常有帮助。国内艺术界迅速摆脱对西方艺术的膜拜,开始认真地走自己的创作道路,是与这种访问造成的认识结果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来访问的中国艺术家在此住上一年半载,深入了解情况,之后也离开了;很难说他们对于西方有什么共同的认识,但是比起第一类的匆匆访客来,他们的认识就深刻多了。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共识就是:在西方,当个完全靠艺术为生的艺术家非常困难。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另外的一些艺术家。他们移居西方国家,应该说对西方艺术的了解比上面两种类型的人都要深刻。其中有少数也能够进入西方艺圈,或者进入西方商业美术圈,取得艺术上或者经济上的成就;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艺术家的身份进入西方主流艺术的极为少数的一群。但是,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虽然努力探索,努力奋斗,但是却依然处于主流艺术圈或者商业艺术圈以外,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原来在国内还以地区、学院或者画会形成群体,能够互相交流切磋;到西方定居以后,这种机会基本完全不存在了。由于各人的生活环境不同,即便是原来在国内形成的团体或者群体关系到西方之后很快就解体了。国内的政府供养体制不存在了,大家要为生计忙碌。有些改行,有些虽然还在画画,但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经常聚会,讨论艺术。虽然来西方的中国艺术家总人数有近千人,但是在西方分散的国度中很快就消失了。所谓中国在海外的艺术家,其实很难从艺术上、或者简单从种族上被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更谈不上作为群体的艺术特征和风格。其中大部分很难单纯靠艺术维持生计;其实西方能够单纯以艺术为生的艺术家的比例电非常低,即便能够如此,也很难保持自己原来在国内发展起来的风格,走原来自己的创作道路。他们或者受当地西方艺术的影响有所改变,或者在自己原有的风格基础上作适合当时当地的某种改变,以适应新的艺术环境或者市场环境的要求。由于远离祖国,与“根”日益疏远,这样,不但国内评论界开始忘却他们,西方艺术界也不接纳他们,更不会有人专门研究他们的历程,而他们自己中不少人也开始感到对艺术淡漠了。只有极少数一批人能够在困境中奋斗,得到某种程度的进展,取得某种程度的承认,他们的历程是十分艰辛的。
从我个人来说,因为长期在美国的艺术院校担任教学,从事研究工作,生计无愁;况且一直处在西方艺术理论界中,对于西方艺术界和评论界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观察这些奋斗中的艺术家,了解他们的创作意图,研究他们发展的趋向。自己从事艺术理论工作,因此往往不会卷入艺术家的个人交恶,或者某些流派风格等具体意见的出入纷争之中;加上从事艺术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又能够保持与艺术界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与中国旅居外国的艺术家和外国艺术家都保持基本是等距离的关系,比较能够避免过于偏向哪个方面。教书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没有谋生的经济压力,在美国教书更加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比较专门的研究,这大约是为什么我在美国的著作量比在国内的时候要多的一个原因。在美国的十年期间,因为工作特点,我在美国接触过的艺术家不下百人,比在国内认识得更多;我还利用工作得关系为好几位中国艺术家在美国高等艺术学院中举办展览,其中包括1994年为陈丹青、徐冰在我任教的洛杉矶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Design, Pasadena, California)的联展,1993年为陈丹青、刘晓东、肖惠祥、秦元阅、蒋铁峰、唐大康等人在我兼任教学的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Valencia,California)举办的大型联展。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些环境,使中国艺术家的探索得到西方主流艺术的认同。我本人也曾经担任过一些与艺术有关系的社会工作,比如1994年担任过洛杉矶市政府分配的保罗·盖地基金会(Paul Getty Foundation)的艺术基金会评审委员,等等。我一直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够在更多的方面给中国艺术家以支持,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增进外国对中国旅居的艺术家的认识和了解。而我自己,也因为这些活动而对于西方艺术的发展状况和艺术活动的运作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旅居西方的艺术家的状况和他们的艺术探索有了一个较为中肯的认识。
从1992年开始,我为台湾的《艺术家》杂志撰写了《中国大陆现代艺术史》一书,分期在这本刊物中连载了4年。为了这本著作,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对从民国初年到1990年为止的中国艺术发展进行了研究,具体到各个时期的主要艺术代表人物、主要艺.术运动和艺术上具有争议的一系列问题的细节讨论;也利用不断回国讲学的机会逐渐完善和更正一些研究上遗留的、有差错的、不够准确的具体问题,包括访问大量艺术家、深入图书馆查找资料等等,因而,对于国内的现代艺术发展的面貌也有一定的了解。以上这几方面的条件,大约便是我敢斗胆承应贺先生所托的原因吧。
其实,我也不可能对目前旅居西方的中国艺术家作一个完整的介绍,主要的原因是基本没有可能了解到在西方各个国家极为分散的艺术家的全面情况。中国目前旅居西方的艺术家,即便在纽约或者洛杉矶,也基本是各自为政,因此难以对他们的艺术创作了解得十分完全。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希望介绍自己;有些人感到自己的成绩不够,有些人则感到难以自圆其说,或者还不成熟,另外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创作无非是为了谋生的商业活动,不值一提。特别是有些庸俗的商业画家回国大吹大擂,宣传自己的收入,更加使一些具有术家基本良心的艺术家对于在国内的介绍望而生畏,好像一旦介绍自己,就加入了这类的行列。他们当中一些人的作品,仅仅是为生的劳动,而非个人艺术的探索,因此,也难以作为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家的典型来介绍。因此,仅仅是为这本<美术文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对象,就非常困难。加上我本人所认识的海外艺术家,虽然人数不少,但是比较接近的大部分人都是旅居美国的;与旅居欧洲和加拿大的一些艺术家虽然关系很好,但是路途遥远,除了电话联系之外,联系很少,因而对于他们的创作情况很难有真实的把握和了解。比如四川画家程丛林去年来洛杉矶,我和他以及高小华等人一起吃饭,他谈到自己还是在画画,但是画些什么,却没有可能见到;毕竟他住在德国汉堡,实在太远。去年秋天,我到法国出差之前,杨诘昌在电话中邀请我去他那里住,但因为在巴黎活动紧张,也不得不放弃他的盛情邀请。对于他最近的创作,我与其他读者了解得差不多,都是从1996年11月的台湾《艺术家》杂志上通过侯翰如的介绍得到的,我自然不敢介绍。如此种种,局限甚多。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仅仅能够从我比较了解的一些艺术家中选择自己认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这种选择,自然会有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这里提出的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如有偏颇,文责自负。
1.中国旅居海外的艺术家的基本情况
国内旅居西方的艺术家可以粗略地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完全脱离艺术创作而改行的。他们大部分并非自愿改行,而是因为生活原因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热爱的工作,或者从事纺织品设计、平面设计,或者从事与艺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第二种则是转向商业艺术工作。西方商业艺术和严肃艺术(他们称为“试验艺术”)是泾渭分明的两个范畴,商业艺术的服务对象是大众,严肃艺术的服务对象是收藏家、博物馆。虽然大部分艺术家都希望能够进入严肃艺术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有自己运作的规律和理论模式,与仅仅是为了取悦于感官的商业艺术大相径庭,这对于在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上与西方艺术家差距都很大的中国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们中间有一些驾轻就熟地利用自己娴熟的写实技巧或者装饰技巧而进入了商业美术领域,其中、少数人在经济上取得相当不错的收获,即便在西方也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第三种类型是在严肃艺术的途径上探索的一群。他们的道路非常艰苦,而且很少得到认同,其中有极少数人取得一点成功,而付出的代价却是非常大的。以上几大类型的艺术家当中,又有不同类型的探索:其中,走严肃艺术探索道路的一批人,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的若干潮流派的影响,特别是新表现主义、新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抽象绘画这几一风格流派的影响,而基本在这几个方向上发展,并且少数人开始进入主流;另外有一些人则完全按照自己的喜爱和习惯,作自己的创作,不西方或老东方的潮流,自成一统,独立发展;还有一些艺术家则完全是走商业艺术路径,包括相当庸俗的商业艺术风格。在这个类型中,为艺术的目的非常微弱,主要的支配力量是经济性的。因为是商业艺术,所以经济效益有时相当不错,甚至利润丰厚,但其作品却没有任何严肃艺术意义上的价值,不可能在艺术评论中有任何地位。(比如兰国内曾经很有影响的“云南画派”的重彩画,在整个西方的严肃艺术界和评论界就没有什么地位。几乎没有严肃的评论家会出席他们的展览,也没有严肃的艺术出版公司会出版他们的作品,博物馆也不会收藏他们的作品,连正式的美术学院也不会举办他们的展览。)严格地说,商业画家与房地产商人的地位相似。真正引人注意的是从事严肃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的探索历程和他们的发展方向。
国内自“文革”后移居西方的艺术家,主要集中在西方的一些大都会中,只有少数是在比较小的城镇生活和工作。大都会有比较方便的交通,有艺术专场,也有比较多的中国人,无论从艺弋还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说,都比那些中国人很少的小城镇方便。在西方大部分国家中,又以美国和加拿大集中的人最多,特别是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多伦多、温哥华、芝加哥这些城市,都有上百的中国艺术家。如纽约和洛杉矶,中国艺术家的数量超过百人,是真正的大本营。这些大城市都具有相兰数量的艺术博物馆、艺术学院、画廊;有些城市还出现了由中国人开办的、针对华人社区的画廊,因此,对中国艺术家更加具有吸弓『力。我所认识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是在这些大城市中的。对比来看,住在欧洲的中国艺术家则比较分散。1995年秋天,我在巴黎到旅居那里的两个很杰出的艺术理论家和活动家侯翰如和费大为。我在巴黎中国人居住比较密集的拉齐兹神父公墓附近地区的街头咖啡馆聊天,他们介绍的一些我知道的艺术家,都不是住在巴黎市中心,而散居在西欧各个地区。杨诘昌算是住在巴黎了,但是也在很远的郊区;不像纽约、洛杉矶那样集中,更不会出现那种完全依附于华人社区的什么“海外中国艺术家协会”之类的组成形式。但是,即便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中国艺术家,也基本处在各自为政的地位,什么“画会”、“协会”,不是因为某种经济目的成立,也往往有其复杂的人事背景,大部分是借艺术来做其它的事,称不上是真正的艺术群体。因此,中国在海外的艺术家首先是比较独立,或者说是孤独和分隔的,与国内那种人头踊踊的群体热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果要找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来形容大部分在“文革”之后来到西方的中国艺术家的状况,我想可以说,他们是在国内搭上了头班车,在中途下车,想到西方搭更加快的班车,却没想这里车站乱匕八糟,不知道哪班车才是他们想搭的特别快车,因此各自抢上车,有些搭错了,有些勉强搭上乱匕八糟的西方当代艺术的末班车(未必是特别快车),有些根本连车也搭不上了。这样,有些人就停留在车站上等候下一班车,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车;另外一些人则离开了车站,不再想上车了;还有一些人虽然明知道搭不上车,却希望能够利用其它方法前进,于是努力找寻可以替代的交通工具。原来大批来到西方艺术车站的中国艺术家们,就这样分散了。这样形容艺术家们,可能过于刻薄,但是从整个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却有它一定的道理。
到1979年,国内就开始了开放改革,艺术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创作高潮。各种艺术群体运动纷纷涌现,北京的油画研究会、上海的“十二入画展”、北京的“星星画展”等等,都开始了非常个人化的艺术探索;这种探索很快发展出几个新趋势来:对于传统水墨画的探讨、对于传统艺术价值的研究和争论、对于西方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现代主义运动的绘画和雕塑的各种形式主义的模仿。到1985年在安徽泾县举行的油画研究讨论会,也就是所谓的“黄山会议”时,开始了比较深一步的对现代艺术的实质的探索和了解,逐步推进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把西方整整用了100年发展的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都夸张地同时以中国的方式展示出来。在从1979年到1989年这个短短的10年中,国内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艺术浪潮和群体运动,比1949年解放到“文革”结束时期为止的所有探索的总和要多上不知道多少倍,国内的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也出现了空前的混乱。除了年纪比较大的一辈艺术家以外,中国大部分艺术家都与这个时期的浪潮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关系,其中年纪比较轻的那些,更是推波助澜的中坚力量;这个时期出国的艺术家,也以他们为主。从引发1978年“首都机场壁画风波”的袁运生和参与壁画创作的肖惠祥,1979年上海“十二入画展”的主要人物之…的孔柏基,1979年北京油画研究会的积极的参与者中的秦元阅、周菱、汲成等人,1980年在北京引起震动的云南十入画展代表人物蒋铁峰、姚仲华,1979年前后出现的新写实主义绘画高潮时涌现的新人陈丹青、陈丛林、白敬周等等,1979年“星星画展”的主要人物王克平、钟阿城等等,直到80年代末在艺术观念上影响很大的徐冰、谷文达、吴山专、黄永砅、杨诘昌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开创先河的风云人物。这个名单可以列出数百位艺术家来,代表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家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目前仍然在西方,特别在美国。这一点,我在写作《中国大陆现代艺术史》的时候非常有感触:凡有什么细节不清楚,晚上打电话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就基本能够找到这个10年中中国艺术运动的当事人了解。1989年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几个组织者和主持人现在都在美国,我对于这个展览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们。这种大批艺术家移居海外的情况,在中国可能史无前前例。
(本文发表于1997年《美术文献》总第9期)